*转自“鹤鸣古典社”公众号。
编者按:今天是著名学者刘咸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本社特别推送二篇文章,以寄追念敬仰之情。先生名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成都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先生家学源远流长,祖沅,父梖文皆为蜀中知名学者,自1916年起先后任教于成都尚友书塾、敬业学院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先生一生著述颇多,计已成书的共236部,475卷,总名《推十书》,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佛学、道学等方面,另有后人编辑《刘咸炘学术论集》传世。先生于史学、校雠、目录、文学等均有杰出成就,特别对于四川学术文化教育有卓越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北宋政变考
戊辰十月廿日修补
刘咸炘
政事出于人才,人才起于风气。故观风气者,读史之要也。风气之总要,阴阳刚柔动静而已。刚动之世,其人热,类墨翟,其治张,必归刑名,其弊为躁争。柔静之世,其人冷,类杨朱,其治弛,必尚黄老,其弊为疲懦。大道不明,畸偏致害。二者相矫相乘,数千年而不止。战国动而汉初静,西汉末静而东汉末动,唐静而五代动,皆彰彰也。北宋承五代,初静而后动,转关在仁宗之时。真宗以前静,英宗以后动。新旧相争,门户朋党起焉。君子小人是非淆乱,当世已罕公论,后世益复追逐偏听。能超然知其始终者,前惟朱元晦,后惟王而农。然犹多未尽明。欲观北宋之风,必求诸杂记小说,单词片语,往往可推见其大。两造毁誉,亦后世所宜参听也。正史既不尽取,虽取亦不能发明,是以后他论者,但知誉仁宗而毁神宗。称李沆、王旦为贤,而不知其流为吕夷简、章得象;诋王安石为奸,而不知其源于范仲淹、欧阳修。议论愈多而情势愈晦矣。壬戌八月,略览宋世杂记书,就所见采录,分为五段。段系以题,或条加数语,并引朱子之说,王氏《宋论》,则不复赘录。《宋史》无佳本,今录虽略,已具变迁之梗概,其余人才议论,皆可以此推之。虽不敢谓具史裁,亦读史之要删也。因论史识总纲如上。
第一段 太祖用柔道抑武人,赵普佐之以猜忌。太宗承之,大用文士,重文轻武,以致武功不竞。
《涑水记闻》曰:太祖受命,问赵普曰:吾欲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唐季以来,战争不息者,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云云。杯酒解兵柄事详正史,不具录。
又曰: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谕曰:功成,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归。太祖曰:今未服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战耶?姑徐之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又曰:诸藩镇罢归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道旧甚欢。太祖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以上均又见《曹氏闻》。
《闻见近录》曰: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闻见近录》曰: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故常,取于民无节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赐饮款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为钱几何?方镇具陈之。上喻之曰:我以钱代租税之人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相宴乐何如?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至今侯伯尚给公使钱,以此也。
又曰:太祖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题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
《浙山野录》曰: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东原录》曰: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
此足见太祖知文士之无用,与汉武用公孙宏同意。
《王氏默记》曰:国初,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
《邵氏》载范质《戒子孙诗》,大旨戒勿多言,勿任侠。邵氏又曰:祖宗宰辅,皆忠厚笃实之士。
太祖所用范质、王溥,乃冯道、和凝诸人之传衣钵者。冯道有《长乐老自叙》,王溥有《自问诗叙》均见《容斋三笔》。此诸人沿唐人之习,大抵以柔厚保位。吴处厚《青箱杂记》最能表其风气。其书颇辨道之非依阿。又处厚论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朝廷台阁之文,温润丰缛,正谓官样与富贵气者,皆此一派之传也。《处厚书》又载道诗及张齐贤《自警诗》及《邵氏闻见录》载质《戒子孙诗》,旨意略同,皆主宽厚谨慎,所谓格言入于乡原者也。又言于诗爱白乐天,又爱冯瀛王,此足见北宋初诗之多宗白及《击壤》一派所由起之故。宋初人多称冯道,虽以石介之好诋,亦谓五代大坏,瀛王救之。《青箱杂记》称冯道《东轩笔录》谓王荆公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能改斋漫录》谓富郑公、苏黄门以大人称道。《晁氏客语》谓逍功高而名节非也,尝以管仲为比。
叶氏《避暑录话》曰: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喻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又曰: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又曰: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自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率以得士多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几二万,自后未有如是盛者。
《石林燕语》曰:太宗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
《朱子》曰: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
按:《避暑录话》载所撰诗甚朴陋,本非文士,岂真好学哉。
《野老纪闻》曰: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自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记闻》:庞籍奏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又引《东轩笔录》曰:青在枢府四年,每出,军士必指以相夸。又引《王尧臣墓志》曰: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属目,往往造作言语以相扇动。又《东轩笔录》、《东斋记事》、《石林燕语》皆记当时谣言青之异迹。《石林燕语》、《渑水燕谈录》亦载苏绅、孔道辅言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
《王氏默记》曰:韩魏公帅定州,狄青为总管。魏公抑制之。后青为枢密使,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太祖承五代兵骄之后,以柔道收舍之,不可谓不能。然收郡县兵,轻武臣,后有危难,遂无所赖。北宋名将,仅王德用、狄青,皆被谗谤,几于不免。王氏论之详矣。罗大经亦言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最弱,皆缘官自养兵,故张魏公置义勇,陈福公行民兵之策。
《元城语录》曰: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澶渊之役,章圣既渡大河,至浮桥一半,高琼执御辔曰: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盖当时宰相王钦若、陈尧佐辈好诗赋,以薄此辈,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语。
第二段 真宗朝承旧法,李沆、王旦辅之以柔静,而泰久生侈,愈疲弊。
苏氏《龙川别志》曰:真宗初即位,李沆为相。帝雅敬沆,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帝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故终帝之世,数人者皆不进用。是时梅、曾皆以才名自负,尝遣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致尧疏论仲舒,言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然沆在中书不喜也。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梅询躁竞事见《涑水记闻》。
又曰: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若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矣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及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邵氏、朱氏及王氏《渑水燕谈》、马氏《元城语录》载此事微异。
《元城语录》记李沆不上便宜及白四方灾变,引《魏相传》证之。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谈苑》曰:李沆在相位,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其弟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奏论,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自余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为我谢马君。沆常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
刘元城《语录》曰:李丞相每谓人曰:但诸处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时经变多矣,故所立法度极是稳便。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其利多耳。
《邵氏闻见录》曰:国初,赵中令于听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人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则焚于通衢。李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矫激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报国耳。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
朱子曰:《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兴起至治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谈苑》曰: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于宽猛得中。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净之化。又引《事实》曰: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质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察之则无所容,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
黄震论蒙正曰:清心省事,似从道家来。
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弛之才,乃至论文主馆阁体,论诗主白居易,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大抵唐之余也。吴处厚《青箱杂记》全为此等议论。丁晋公《谈录》亦然。故称李侧之效白诗及诸老之风鉴,称冯道诗谙理而辨其非依阿,道诗略如白居易。皆所谓乡原也。
仁宗承旧,亦于外患皆主退让。后广开言路,新派范、富、欧诸公起,与旧派吕、章等相倾。士气遂动,多言更张。程、司马、苏、王诸人由此兴。以下分述之。
一旧派吕夷简、章得象、晏殊、张方平。
王氏《渑水燕谈录》曰:王沂公当轴,以厚重镇天下,尤抑奔竞。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焉。
朱子曰: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
《孔氏谈苑》曰: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
《涑水记闻》曰:上与吕夷简谋,以夏辣等皆章献太后党,悉罢之。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遂并罢之。后夷简竟谮废郭后。
又曰:吕相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例。谓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
黄老家必主法,吕多机智,事散见各书 。孙沔上书劾其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比之张禹、李林甫。
《王氏默记》曰:晏公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如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后罢相,曰: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与之为敌,不保其终,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
能容于物,即旧派黄老之术也。
《麈史》曰:宋元宪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静,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公尝自谓时贤多以不才诮我,因为《自咏诗》曰:我本无心士,终非济世才。虚舟人莫怒,疑虎不当开云云。
王巩《闻见近录》曰:张文定尝云:在翰林时,当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贺之,因语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谢事也? 百书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时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则忘了矣。文定与景文相顾而笑。退而相语曰:是何言欤?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为然。盖在得之时,与夺每为思虑所惑,不若少时能断。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后,遂屡请归。予尝论之,阳舒而阴敛,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阳衰面阴盛,变是以好敛之意生,君子终始之际,可不慎乎。
此即黄老之术。王巩乃王旦之孙,又与东坡契,故尊得象、方平之传也。
《龙川别志》曰:章郇公为人厚重。吕许公薨,遂秉政。晏元献、杜祁公、范文正、富郑公更用事,公默默无所为。然数公既去,而为相如故。
《闻见后录》曰: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后二公阅历岁月,经历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又见《闻见后录》,作张文定问郇公语。
章得象谗中范公事,见《涑水记闻》。
《老学庵笔记》曰:苏子由晚游许昌贾文元园,作诗云:前朝辅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盖谓方仁祖时,士大夫多议文元,然自今观之,岂易得哉。
以上数条,可见旧派之风旨。
旧派本相传授,王曾为李浣沆婿,王旦为赵昌言婿,韩亿、吕公弼为王旦婿,曾公亮、贾昌朝为陈尧咨婿,原缺富弼为晏殊婿。
宋氏兄弟乃夏竦所识拔,见《石林燕语》。《青箱杂记》谓贵人能知贵人。《却埽编》谓公卿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者是也。
旧派人多奢侈,如寇莱公、宋景文。
旧派之风,以厚重为长,盖远自唐之牛僧孺等,至宋则丁谓以降皆然。其中多长德,而亦多奸诈。其与新派之不合,亦正如牛、李之不同也。
旧派从道家亦甚显,晁迵之书不待言矣。宋景文笔记庭戒诸儿,亦言道家清净柔弱,行之不害为儒。
叶氏《进暑录话》曰: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王氏默记》曰:欧阳公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公锐意言事,疏斥晏、章等,大忤权贵。
《涑水记闻》曰:余靖、尹沫以论救范文正,坐贬。欧阳永叔贻书贵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若讷怒缴其书,降夷陵县令。永叔《与师鲁书》曰: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怖,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
《默记》曰:张公安道尝为子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国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天下。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李迪以落韵,贾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犹持此论。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许公虽复作相,然不能守其旧格,意虽不喜而亦从风靡矣。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人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郑公尤倾身下士以求誉。相帅成风,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傲诞为高。于是私说遂盛,而朝廷轻矣。然予以张公之论,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见今世朝廷轻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弊也。大臣恣为非横而下无由动,其害亦不细也。使丁晋公之时,台谏言事必听已,如仁宗中年,其败已久矣。至于许公,非诸公并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盖朝廷之轻重,则不在此。
叶适《习学记言》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已。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即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譁然不安,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罗氏《鹤林玉露》曰: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轻哉。韩公为侍从,则能攻宰相;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我之盛德。濮园之议,欧阳公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乃欧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已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
以上二段两造说当兼听。张、叶亦非尤见,不可概非。
《涑水记闻》曰:嘉佑四年,上手诏两府。先是两制臣僚不许至执政私第,两府大臣奏荐人不得充台谏官。凡此条约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际,了无疑间之迹。
王氏《麈史》曰:御史人台,满十旬未抏章疏,例输金以佐公用,谓之辱台钱。神文朝一御史,供职余九十日矣,未尝有所论列,盖将行罚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众伫听,以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误有遗发于其间者。御史皆以才举,所议如此而无责,盖朝廷务广言路耳。
此所谓寻题目也,正广开言路之弊。
朱子曰: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又《语类广》曰: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日议论胜亦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亦不过说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吴处厚《青箱杂记》曰:皇拓、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石林燕语》曰: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
《涧泉日记》曰:韩魏公言:挺然忠义,奋不顾身,尹师鲁之所存也。身安,国家可保,明消息盈虚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问二公,公曰:立一节则师鲁可也,考其终身,不免终亦无所济。若成就大事,以济天下,则希文可也。
王氏《默记》曰: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及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弊。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改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仇。
《名臣言行录》引《韩魏公别录》曰: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公与范公适自陕西来朝,道中得之。范公附股谓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坏。
叶氏《避暑录话》曰:石守道与欧公同年进士,为《庆历圣德诗》,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佑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更历而后尽其变也。朱子曰: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 梅圣愈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公为相,子美为馆职,为会请诸名胜,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尽招女伎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伺败阙,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命中官捕捉,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几个轻薄做得不是。
以上数条,见新派亦有过处。
新派范仲淹、孔道辅皆晏元献所荐。见《石林燕语》。
《后山谈丛》曰:某公即吕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军兴,以韩、范为西帅,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实间之。又不克,军罢而请老,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党贾文元、陈恭公间焉,犹欲因以倾之。
《名臣言行录》引韩忠献《家传》曰:庆历中,公与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辅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时张方平、钱明逸、王拱辰为两制,皆历中丞。故杜祁公而下,为三人者排逐,指为朋党,相继罢去。是时二府许逐厅见宾客,拱辰未见,因讽劝公,奋手作跳踟势,曰:须是跃出党中。公对琦惟义之从,不知有党也。既而公亦求去位。《注》引《遗事》曰:公惟务容小人,善恶黑自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公安焉。后扶持诸公复起,皆公力也。
孔氏《谈苑》曰:韩稚圭教一门生曰:稳审著,大事将作小事做,小事将做大事看。
《朱子语类》曰:司马温公为谏官,与韩魏公不合。其后作《祠堂记》,极称其为人,岂非自见熙、丰之事故也。韩公真难得,广大沈深。
《龙川略志》曰: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许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以参知政事安抚陕西,许公既老居正,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许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许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之乃信。
叶氏《避暑录话》亦载撰碑事,辨其实有。且曰:欧作《碑》,屡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盖是时吕许公客尚众也。
《朱子语类》曰: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又为《百官图》以献,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曰: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补过之功,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
欧公自言此事见《墨庄漫录》。谓范公和解之语,明在集中云云。
《龙川略志》曰:中书舍人缴还词头,自富郑公始。吕许公以非旧典不乐,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类也。
《名臣言行录》引《魏公别录》曰:公言章得象在中书时,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与希文、彦国以文字至,两府辄闭目不应。彦国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体,不许也。
《邵氏闻见录》曰:富公再使,以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驰还奏曰:政府固欲置臣于死。仁宗召吕夷简面问。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富公益辨论不平。仁宗问晏殊如何书,曰:夷简绝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
《邵氏闻见后录》曰: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
朱子曰: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
朱子曰:吕夷简最是无能。其所引援,皆是半闲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邵氏闻见录》曰: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公同年进士,同为薛氏婿,文忠心少之。盖懿恪主吕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党不同云。
《避暑录话》曰: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面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
《老学庵笔记》曰: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文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日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
《言行录》引《苏氏谈训》曰:张安道雅不言石介,谓狂谲盗名,所以与欧、范不足,至人且以奸邪。
《名臣言行录》引《荆公自录》云:神宗尝言方平少时好进,尝自干仁宗求为执政。荆公言方平为御史中丞,专附贾昌,朝误仁宗,赏罚甚众。
《朱子语类》曰:张安道为人不好,尝托人买妾,受之不偿其直。其所为皆此类,是个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为正人所恶,那边又为王介甫所恶。盖介甫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简放恣惯了,才见礼法之士必深恶。论来介甫初间极好,后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几个如何及得他。
《邵氏闻见录》云: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诋毁云。
当时议论,以仁宗比汉文。
《邵氏闻见录》曰: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何如唐太宗?众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
凡主柔静者,皆不主法三代,汉文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也。
刘延世孙公名升。《谈圃》曰:苏子瞻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传尧俞、王喦叟言,以文帝为有弊,则仁宗不为无弊;以宣帝为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
神宗行新法,用王氏经术,矫先之柔懦,欲复外患之耻,更张因陋就简之法。司马、范、程诸人与王氏争,不胜。
《涧泉日记》曰:仁庙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为。神宗早年,大臣欲作为,小臣多持重。
《王氏默记》曰: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故滕章敏首被擢用。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债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尤甚。
《邵氏闻见录》曰: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廿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
《邵氏》曰:未开熙河前,关中人士多言河湟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以取。仁宗朝,韩、富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
欲取者非不是,不纳者恐生事。
朱氏《曲洧旧闻》曰:神宗喜谈经术。
又曰: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其术传贾文元。介甫经术,实自文元发之,而世莫有知者。在馆阁间谈经术,虽王公大人,莫敢与争锋,惟刘原父兄弟不可少屈。
马永卿《元城语录》云:先生与仆论变法之初,仆曰:神庙必欲变法,何也?先生曰:盖有说矣。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然其实于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庙即位,天资绝人,是时见两藩不服,及朝廷州县多舒缓,每与大臣论议,有怫然不悦之色。独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以激切奋怒之言以动上意,遂以仁庙为不治之朝。神庙一且得之,以为千载会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则太后,外则顾命大臣,尚不能回,何况台谏侍从乎。
朱子曰:自来立法建事,不肯光朋正大,只是委屈回护,其弊至于今日。略欲触动一事,则议者纷然以为坏祖宗法,故神宗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
朱子曰:神宗极聪明,真不世出之主。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又曰:神宗聪朋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间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所著论,有云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日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又撞著介甫出来承当,所以做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却又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又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敌骑所过,莫不溃散。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耳。
曰: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
又曰:温公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
又曰: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
又曰:《吕氏家传》载,荆公当时与申公极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来,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了初意。又云:子由初上书,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叶氏《避暑录话》曰: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中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仇。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遂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陈氏《扪蝨新话》亦载此事。且云《辨奸论》、《王司空赠官制》皆苏氏宿憾之言,荆公谓老苏文有纵横气。赠官制当元祐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以此知王、苏之憾,不独论新法也。然后学至今莫不党元祐而薄王氏,宁不可笑。
苏氏本近旧派己见前。
此二说皆实录。后世论者不信,误矣。王评苏亦当。
《邵氏》曰: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后录》曰:东坡中制科,王荆公谓吕申公曰:苏氏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
《龟山语录》曰:因论苏明允《权书·衡论》曰:观其著书之名已非,岂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于用兵。如此所见,安得不为荆公所薄。
《道山清话》曰:老苏初出蜀,以兵书遍见诸公。富韩公曰: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做。
《朱子语类》曰:东坡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后来更不复言用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又曰:荆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日、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
又曰: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说。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模样。近他吕伯恭亦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然老苏诗云: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中来。如此无所守,岂不如他荆公所笑。如《上韩公书》求官职,如此所为,又岂不如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但用之不久,故许多败坏之事未出。兼是后来群小用事,又费力似他,故觉得他个好。
《邵氏闻见录》曰:司马温公、王荆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绝交。《邵氏》所记甚详。
又曰:介甫平生待吕惠叔甚恭。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之,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恶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康节谓申公曰:王介甫者,远人君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
又曰: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却埽编》曰: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来谈燕终日,他人罕得面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又曰:富公过南京,张公安道迎谒。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朝,某知贡举,辟安石,考校既至,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富公俛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荆公。
叶氏《避暑录话》曰:欧文忠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王荆公也。
《元城语录》曰: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学问。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谓温公。略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者尔。而诸人则溢恶,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毁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学乖僻,用之必乱天下,则人主必信。若以为以财利结人主如桑宏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卢杞,大佞如王莽,则人不信矣。《邵氏》曰:范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元城语录》曰:老先生尝谓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在清要,或在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用老成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仇敌,他日将悔之。介甫默然,后果有贾金陵者。
《邵氏闻见录》曰:程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但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
又曰:初行新法,天下骚然。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先公。先公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先公不以清激取虚名如此。
元祐废新法,用司马,而程、苏、刘诸人自相争,分为三党。
《邵氏》曰:神宗升遐,遗诏至洛。韩兵部宗师问程宗丞伯淳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
又曰: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叜、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汕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深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王玉山《答李逢吉书》曰:元祐诸公,忠直有余,而识见不足。
《朱子语类》曰:元祐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盖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
又曰: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诸公尽罢之,却是坏其已成之法。曰:固是。人杰云:如弃地与西夏亦未安。曰:当时如吕微仲自以为不然,其他诸公所见,恨不得纳诸,共坏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
又曰: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又曰: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大峻急。
又曰:元祐诸贤,多是闭著门说道理底。后来见诸行事,如赵元镇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矣。
又曰: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诉所,令熙、丰间有所屈抑者尽来雪理,此元祐人之过也。
绍圣复行新法,用小人,尽斥前三党。自此以降,更互进退,政局屡变,以迄于亡。已详正史,兹不赘录。
叶氏《避暑录话》曰: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余在江东,兼领淮西事。淮西收复,郡前率用招降盗贼,就付之,安于凶残,至缚人更相馈以为犒设,此前世乱亡之极未有也。余力察而禁之,且言于秦丞相,幸朝廷大为约束。会余罢帅,不能终。此曹如犬豕,吾士大夫何至渐渍此习乎。
又曰: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自夷狄暴起,东南州郡类以兵不足用,且无器械,望风而溃者皆是。
叶虽王党,而此论则是。
罗大经《鹤林玉露》曰:秦桧见高宗,首进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稍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日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意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
按:桧收兵柄事,见《山房集》及《齐东野语》卷十三。
《老学庵笔记》曰: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榜状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榜子,几与胥吏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晓晓久之乃已。
按:此皆南宋复言兵而不及之状也。
又曰: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势险固。太平兴国中,丁晋公为转运使,始迁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关,使于白帝屯兵,下临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则夔帅不能亲将,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夔州必随以破,可谓失策。大抵当时蜀已平,乃移夔州;晋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晓。若使晋、蜀复为豪杰所得,彼能据一国,独不能复徙一城以就形胜耶?
后世人主,惟恐人叛之,收兵徙城皆此意,而亡亦在此。
附:
苏氏《龙川别志》曰:太祖功业日隆,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颕。今淮南都园,则溥所献也。
《涑水记闻》曰:将北征京师之人,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于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嘿嘿而出。
又曰: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瓮牖闲评》曰:方北征未行,群公祖道芳林园。陶谷坚欲致拜,曰:回来难为揖酌也。则此事当时已知之矣。
王氏《默记》载李后主赐牵机药以死事甚详。又载龙衮《江南录》一本云:李后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随命妇人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
《邵氏闻见录》曰:李王、钱王皆生日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宋祖之篡,盖有夙谋。太祖猜忌,诸降王死非正命,史讳不书,佚见他说,今撮附于此,以正后世雷同,称为不得已,及宽仁者之误。
本文收录于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二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赵君儒
相关煕强幸小周后图的扩展:熙陵幸小周后图 谁能告诉我 本画肯定是宋代画的,而且"熙陵"这一称呼是因宋太宗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而来,所以画应为赵光义死后,即真宗朝好事者根据传闻所画.且其后又有人临摹再作..不止一个版本....纯属个人意见至于后世,如楼主所说的两处下落,本人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因为从资料所知粉本的图卷,据说清初还能看到,其后就再也没有了。 有人认识研究宋代文化的程民生、张其凡、贾玉英、马玉臣诸先生,曾问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不存了,孔学先生是专门研究宋代史料的,他也这样说。 所以根据这些真迹估计清之后就已经遗失了,而且记得原来中央二台鉴宝节目也提过此画,当时也说只有仿品存世。但是至于楼主看的是什么时候仿得就不好说了,毕竟楼主在网上只有一个图,即使是大家也很难辨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看到的肯定是原画的仿品,不是现代根据史料所作。 今天煕强幸小周后图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后,是否找到相关陵幸小周后图的答案,想了解更多,请关注www.yfnsxy.cn聚上美世界奇闻怪事网站。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首页【QQ秒回】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转载请说明来源于"聚上美",本文地址:https://yfnsxy.cn/sjqw/106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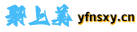 聚上美
聚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