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阿富汗青年华赞决定留下来。
8月19日,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的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而此前,塔利班发言人称,寻求建立一个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包容型政府,将允许女性独自外出、接受教育和工作。
尽管如此,不少阿富汗人仍对未来感到不安,一些人想方设法逃离。在喀布尔一家电视台做平面设计的阿里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的同事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当天,就搭乘飞机去往伊朗,而他和家人因为支付不起签证费用,只能留在国内。
塔利班几乎清一色是普什图人,由于民族和信仰不同,哈扎拉人瑞福担心成为袭击的对象,15日晚,他和妻女打扮成塔利班人,连夜逃往了城外。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8日,土耳其东部城市比特利斯,一些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夜宿深林。文中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人民视觉和澎湃影像。
在家境富裕的华赞周围,许多朋友离开了祖国,唯独他留了下来,“国家像妈妈一样,不能因为妈妈生病了就离开她”,他说。
事实上,阿富汗境内不同的阶层、民族、性别,对塔利班的态度是分化的。在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中国人孙飞在朋友拍摄的视频里看到,塔利班的车辆驶过街头,人群中爆发一阵欢呼。普什图人聚集的坎大哈被认为是塔利班的“精神家园”。
在facebook上很难找到支持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在坎大哈经商的孙飞告诉记者,不少塔利班的支持者是底层民众,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说英语,也很少有机会上网——当地上网费用昂贵,几乎可以占到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这样多侧面和多层次的阿富汗,每一个人面对剧变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7日,土耳其比特利斯省,一群自称来自阿富汗的年轻男子。他们称穿越阿富汗的邻国伊朗到了土耳其。
逃离阿富汗
8月15日晚间,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此同时,许多阿富汗人涌入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他们的国家。
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相互托举着翻越外墙进入机场。机场内,大量无法登机的民众攀爬上机翼或飞机顶部。当飞机缓慢滑行时,一群又一群追赶的人,像是在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2021年8月16日,喀布尔。阿富汗妇女与孩子们在喀布尔机场停机坪上,试图搭上一班飞机逃离喀布尔。
28岁的阿里夫也在努力寻找“救命的稻草”,但他觉得攀爬飞机逃离只是徒劳。
当地时间16日,阿里夫对澎湃新闻说,能从阿富汗安全撤离,意味着拥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势”,就像他2016年从喀布尔的多媒体学院毕业,找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花费了三年时间,“在喀布尔找工作,需要有分量的推荐信,而非文凭”。
他和母亲、姐姐一同生活在喀布尔。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每月有近一万阿富汗尼的收入,相当于近一千元人民币。他唯一一次出国经历,是去印度照顾生病的妹妹。
在他的印象里,塔利班更关注伊斯兰文化,而非教育和进步,对方会用暴力侵害妇女。他还小时,大人们就用“塔利班来了”吓唬他,以至于当塔利班真的来了,他本能地想要“逃命”。
受西方文化影响,当地媒体有不少反对塔利班的声音,一想到“塔利班讨厌为媒体工作的人”,他就感到害怕。他有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同事中有人已经离开,从伊朗非法入境到伊斯坦布尔。但他没有足够的钱带着家人撤离。如今他只能每天查找愿意接收阿富汗难民的国家名单和申请难民的条件。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9日,伊朗东南部,大批从阿富汗逃离的难民聚集在阿富汗和伊朗的边境地带,试图进入伊朗。
在facebook上回复澎湃新闻的七名阿富汗当地人,包括阿里夫在内,都不约而同问道,“你能帮我解决难民问题吗?”他们同时告诉记者想要撤离的家庭成员数量。在得到否定答案后,多数人便不再回复。
阿里夫称,这次接受采访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塔利班发现我把这些信息交给一名记者,我们会死的”。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1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分析,想要逃离阿富汗的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曾经为美国人服务的,比如翻译人员;一类可能是对20年前塔利班执政记忆深刻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多,能力更强;第三类是在加尼政府框架里的受益者,比如官员、警察、商人、知识分子等。但在环球时报的采访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想要逃离阿富汗的人不一定都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有办法通过边界,这些挤在机场里的,恐怕更多是下层人员。”
澎湃新闻记者16日通过facebook的定位检索功能搜索到的阿富汗青壮年人,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定位到首都喀布尔,记者发现每十个年轻人中,就有两到三位毕业于喀布尔大学,这是阿富汗境内最好的大学。由于在阿富汗谋生手段有限,他们中不少人给外国人做翻译,进入政府及公共部门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
今年26岁的阿富汗人华赞,在喀布尔的凯尔卡纳(Khair Khana)地区,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从中国和伊朗进口地毯、电热毯、家具、衣服、鞋子等,在当地做批发生意。因为塔利班的到来,店铺已停业一个月,运输中的货物无法按时送达,损失达1万美金。他本科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曾到中国留学三年攻读硕士学位,今年6月收到了吉林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他的父亲此前在加尼政府的内务部工作,担任警察,负责保护阿富汗的石油。塔利班上台后,他们担心遭到报复。
当地时间2021年8月9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因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民众逃离家园。
华赞的家族在阿富汗北部贾兹詹省(Jawzjan)开有建筑公司,在战乱中公司一部分被人烧毁,剩下的拉货车和设备车被抢走。“如果情况继续变糟,家里以后的收入会很低,亏很多钱。”
他的很多有钱朋友都选择离开阿富汗,唯独他留了下来。“我用了这个国家的资源,有很多记忆在这里,不管好日子还是不好的日子,都不会离开。”
华赞曾在外国公司担任翻译,可以申请避难。他希望帮助妻子、弟弟妹妹和一名大学同学离开,“他们都很怕,病了失眠了不吃饭,情况很糟也不敢去医院”。
不安的喀布尔
当地时间8月17日,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第三天,塔利班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回应称,为了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塔利班已赦免所有人。“没有人会敲他们的门,问他们是谁,为谁工作。他们是安全的,没有人会被审问、被追捕。”
当日,塔利班发布声明,赦免所有阿富汗政府官员,同时敦促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塔利班控制下的首都喀布尔,街面上出奇的安静。当地时间16日,华赞告诉记者,街头几乎看不到女人,男人都穿着传统服装。大的商场关门了,只有小超市可以买东西。
当地时间16日,华赞拍摄的喀布尔街上很安静。受访者供图。
8月15日晚上,他在商店买东西时,亲眼看到一位在隔壁商店买馕的男子被当街击毙,袭击他的人坐在政府的车上,持有枪支,留着胡子,身着长袍。16日上午,他在公司附近再次目睹袭击,一家书店店主的弟弟被枪支击中胸部,好在没有生命危险。这让他想起自己胸口永远留下的两道伤疤,2011年,在阿富汗北部的一次爆炸中,两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身体,其中一颗子弹距离心脏只有毫米的距离。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战争波及受伤的阿富汗民众,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在阿里夫印象里,塔利班曾多次在喀布尔发动袭击事件。今年6月13日,他发布了一条facebook。配图是一辆被炸毁的小型面包车,他站在不远处的二楼阳台说,“我没事,如果我在车里,现在也许我的身体变成了两半,或者我的脸在燃烧……”
在阿富汗工作的中国人王帅也觉得,喀布尔的气氛更紧张一些。给王帅做过翻译的阿富汗人米尔,8月17日被塔利班敲开了家门。对方询问了他的个人信息,做翻译的经历,并登记在一个本子上。米尔为此感到不安,担心会成为塔利班报复他的依据。
这几天,华赞一家人维持着正常生活,但他却忧心危险迫近。他每天在家看书、下棋、养花,偶尔出门给家人代购食物。以前,这件事由他的母亲或妻子负责,现在,她们都不敢出门。他在加尼政府当过兵的朋友,也把过去引以为傲的军装藏起来,只穿传统长袍。
华赞是塔吉克族人,这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5%左右。中国国家民委主管的《中国民族报》曾报道,塔吉克族主导过“北方联盟”与塔利班进行斗争,该民族在阿富汗的精英阶层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拥有大量的财富。
华赞6岁时,跟随家人移居到阿富汗北部的贾兹詹省(Jawzjan),成年后才回到首都喀布尔。他们一家都受过良好教育,他的弟弟大学在读,妹妹在上高中。他的妻子今年刚满20岁,十几天前参加的高考。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前,她曾梦想就读喀布尔大学的医学院或文学院、法学院,但现在,她不敢抱有任何期待,最差的结果是,“不上大学 ”。
2002年8月,喀布尔。一名阿富汗女工程师完成了喀布尔大学的工程学课程获得了学历证书。
阿富汗塔利班几乎清一色是普什图族人,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占人口比例大约40%。华赞介绍,塔吉克族和普什图族宗教信仰一样,但语言、生活方式、传统服饰都不同。塔吉克族人说波斯语,普什图族人则讲普什图语,两种语言均为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比较而言,普什图族人更为传统。
他向往的阿富汗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自由和民主”,人们被允许保留各自的政治立场,男生和女生可以自由地决定穿什么服饰,接受教育,上街购物,申请出国。他最担心的是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生活退回二十年前。
2019年9月,喀布尔。一名参加总统竞选活动的员工在加尼的宣传广告牌前自拍。
1997年11月,喀布尔。身穿蒙面罩袍的阿富汗妇女经过一家面包店。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建立政权。
“亲切的”巴米扬
2010年,王帅从部队退役,加入一家做境外公共安全保障的中国公司。2018年8月8日,他被外派到阿富汗,在这里工作近三年。他的工作是帮助在阿富汗的中国企业开展项目风险评估、实地勘探。和当地人交流,了解周边环境及当地人对项目的态度。
6月初,王帅接到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撤离的通知,6月27日,他与六十余名同事从驻地巴米扬乘坐包机抵达喀布尔,住在喀布尔的城乡结合部等待撤离。这里每到晚上七八点停电,打开窗户,外面漆黑一片。黑暗里,能够听到枪声,有时就像发生在楼下,直到警察来了,才会中断一会儿。
在喀布尔街头,王帅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贫穷:经常有四五个小孩围住他,只是想让他买下一支圆珠笔,等他从银行取钱出来,沿街的小孩和身着蓝色长袍的女人便会凑上去,希望讨要一些零钱。街边的小贩很多,骡子被当作代步工具。
相比首都喀布尔,他对驻地巴米扬更为亲近。巴米扬省的主体居民是哈扎拉人,“他们和中国人长得特别像,有天然的亲切感。”哈扎拉人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或把妻子做的点心带到工地上分给他吃。“巴米扬当地几乎没有听说爆炸和枪击事件发生。”
巴米扬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也不排斥佛教。2001年3月,巴米扬大佛在被当时掌控阿富汗政局的塔利班催毁。今年3月,在巴米扬举行大佛被毁20周年祭活动,王帅发现这么多年过去,当地人还会为此流泪。
王帅在项目上接触到的巴米扬当地人,大多有生活保障。“他们给中国人工作,普通工人月收入1.2-1.5万阿富汗尼,翻译大概挣4万多阿富汗尼,加班费另算。”但普通老百姓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国外项目,需要通过当地有权势的中间人,将用工名额分配到各个部落,再由各个部落分配。
王帅与塔利班接触不多,但他向记者回忆起同事的一则经历:同事经过阿富汗北部城市萨尔普勒时,遇到塔利班在路口设卡收取保护费,但到下一个路口,出具发票就可以免除再次收费。
“这一点,比加尼政府做得好。”王帅形容,他接触过的加尼政府的警察和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安保人员,遇到外国人会做出搓钱的动作,重复说,“dollar”、 “money”、 “人民币”,“你得假装听不懂,往前走”。
回国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6月30日,喀布尔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公司在喀布尔的驻地,给他们做核酸检测。“公司怕我们坐车去医院路上感染病毒,把人家请来的。”中国驻阿大使馆从3月份开始,在阿富汗启动“春苗行动”,协助在阿的中国公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但王帅没能接种上。“塔利班控制了很多边境城市,包括和喀布尔相连的城市被切割包围,疫苗过不来。”
7月2日,登上厦门航空的包机,空乘人员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他很久没有见过几百张国人的面孔了。当晚11时48分,飞机着陆武汉,完成了消毒、登记、采血等步骤,他们被送到酒店隔离,费用由公司报销。
如果能在阿富汗待到今年年底,他可以多拿到10万元的工资。但能够安全回来,他已经感到满足。他怕家人担心,只是说自己在迪拜工作,阿富汗时间比迪拜快30分钟,“可以混过去”。
躺在隔离酒店的床上,刷着手机里关于阿富汗的消息,王帅觉得一切很不真实。
他会想起,在阿富汗上空盘旋的带有螺旋桨的美军运输机;也会想起在巴米扬旅游景点,一位身披蓝色卡布罩袍,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当地女性;以及在一次画展上,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阿富汗女性向他介绍画册上红海和地中海的位置。
“精神家园”坎大哈
孙飞是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经商的华人,2019年6月,他在坎大哈开了首家由外国人注册的独资公司做贸易,至今已在坎大哈生活了两年。
坎大哈是普什图人的聚集地,早期塔利班的主要领导人均是普什图人,这里对塔利班来说,就像“精神家园”。
孙飞告诉记者,坎大哈的许多民众都支持塔利班。当地时间8月13日,塔利班宣布占领坎大哈。那时,他正在巴基斯坦谈生意,收到在坎大哈的朋友发来的一则视频:城市主干道挤满了围观的民众,他们穿着传统服饰,当塔利班的车经过时,人群中发出欢呼的声音。
坎大哈街上穿着拖鞋,蹬自行车的塔利班成员。受访者供图。
2014年11月,阿富汗坎大哈郊区,阿富汗女孩模仿妈妈的着装,穿着小罩袍在玩耍。
在坎大哈生活的两年里,孙飞很少见到女性上街。去朋友家做客,对方妻子也穿着布卡罩袍。他也没有在街上见过为女性提供的公共卫生间。只有一次,在商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色布卡的女性,站在商店门廊外,怯怯地询问了一下商品价格。“感觉是受过教育,从国外回来的。”
孙飞住在坎大哈一座占地1500平米的别墅里,接触的大多是富人。孙飞做生意认识的军人、警察,因为半年拿不到工资,对加尼政府满腹牢骚。“有个朋友的父亲在前线做警察,被枪击死了,加尼政府一分钱也没补偿。”
因为塔利班驾驶摩托车主导多次袭击,加尼政府曾颁布“禁摩令”。但当地公共交通不发达,禁摩后很多人无法正常上下班。
坎大哈有近116万人口,在孙飞看来,就像由几千个大家族组成,“还处于部落信息化时代,晚上没有电,上网费用高,人与人天天在一起,社交时间非常多。”
他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对方来自哪个国家关系不大。 “主要是看你在那是干什么的,有的欧美人做宝石生意在当地也很受欢迎。”
孙飞不满加尼政府的工作效率,寄希望于塔利班能带来改变——为了办理签证,他曾专程飞到喀布尔录入指纹,原因是坎大哈没有指纹录入的机器。注册企业执照仅需花费40多美金,但他多次往返喀布尔办理相关手续,旅行费用是办理执照费用的十多倍。
通过facebook,澎湃新闻记者很难找到支持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在孙飞看来,塔利班的支持者相当一部分是底层民众,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说英语,也很少有机会上网。在坎大哈,孙飞每月的上网费用达200元人民币,相当于有正式工作的当地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坎大哈民众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务农,务工或从事贸易活动,相比首都喀布尔,他们对加尼政府的依赖程度不高——而在喀布尔,“为政府工作,给外国人做翻译,通过政府奖学金申请出国留学等等,都需要依赖加尼政府”。在孙飞看来,这或许也是喀布尔民众对塔利班上台,更为恐惧的原因。
前几天,他的坎大哈朋友在WhatsApp上对他说,“Come here back,Good days are coming(回来吧,好日子来了)”。
孙飞的坎大哈朋友和他说,“Come here back. Good days are coming.(回来吧,好日子来了)”。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刘昱秀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来源:中国青年网
相关菲拉 维塔拉的扩展:dnf神枪手多少级专职找谁
以前是18级,现在改版以后是15级
今天菲拉 维塔拉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后,是否找到相关菲拉维塔拉第六次的答案,想了解更多,请关注www.yfnsxy.cn聚上美世界奇闻怪事网站。【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首页【QQ秒回】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转载请说明来源于"聚上美",本文地址:https://yfnsxy.cn/shjw/74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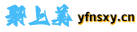 聚上美
聚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