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泰国童妓的扩展: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主义》(1983)
文化主义
Culturalism
作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
译者:陈荣钢(工作邮箱:r.chen20@lse.ac.uk)
引用[APA]: Hall, S. (2016). Lecture 2. Culturalism. In J. Slack & L. Grossberg (Ed.),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pp. 25-53).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钱乘旦等译)
【延伸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首页【QQ秒回】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转载请说明来源于"聚上美",本文地址:https://yfnsxy.cn/shjw/2703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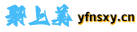 聚上美
聚上美